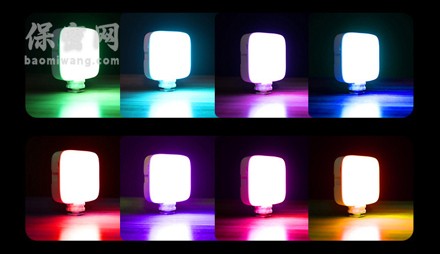如今提到冬季旅游,很多人会想到的就是充满热带风情的海南,椰林伴海风,浪花映骄阳,好一派惬意处得的美好景像。现在的海南,充满了游人们的欢歌笑语,美女们的裙摆飞扬。但是在数十年前,海南,不要说外来人,更是本地女性的恶梦。
放眼全国乃至全世界,海南(旧称琼崖)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的人数之多、事迹之英勇都是罕见的。仅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当地抗日总队的女性党员就占到了部队党员总数的25%,光荣牺牲的女烈士多达1508人。“琼崖女子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在纷飞战火中悄然觉醒的海南革命女性,以鲜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与民族的尊严。追寻这段特殊的历史,记者发现,保密工作作为生命线贯穿始终,串起了所有的故事和人。
在黑夜中举起火把
曾几何时,海南只是一个贫瘠的偏远海岛,男性往往选择外出谋生,而“禁止妇女出洋”的陋习,迫使女子只能留在家中支撑家业、养老携幼。同时,由于孤悬海上,岛内的文化变迁十分缓慢,本土的黎苗“母权制”文化与外来封建父权文化,以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价值观相互碰撞,形成了独特的“女耕男儒”性别关系模式。这意味着曾经的海南妇女不仅要承担烦琐的家务劳动,还要从事重体力生产劳动,所受的压迫较之中原地区妇女更甚。面对付出与回报的严重失衡,海南妇女极度渴望改变,对“妇女解放”存有模糊却强烈的向往。随着五四运动后新思想、新文化的传入,以及共产主义火种的撒播,参加革命以争取与男子享受同等权利,成为摆在她们面前最好的出路。
党组织亦格外重视海南的妇女工作。1926年6月,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口召开,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宣告成立,内设的妇女部也随之创立,由陈三华担任部长。在妇女部的直接指挥下,各县乡纷纷成立了妇女解放协会(支会),干部们广泛组织办学、掀起取名运动、呼吁男女平权,并将农运与妇运相结合,向封建礼教展开了猛烈的冲击。据《琼崖大革命史料选编》记载,当时“全琼崖的妇女,除了极落后的少数偏僻县份外,都把头发剪掉了”,“同时来的还有中老年妇女的放脚运动……几十岁的老太婆也诅咒主张缠足的人了,乡村中从此少了许多乌烟瘴气”。
可惜的是,大革命的夭折,使如火如荼的妇女运动被迫放缓。国民党反动派在海南大肆围捕共产党人,致使我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妇女组织也未能幸免,工作只能由公开转入地下。其间,在早期海南妇女运动中起到突出作用的多位干部被捕,并因不肯与敌人同流合污而惨遭杀害。
比如时任琼崖妇女解放协会委员的冯爱媛。她与丈夫雷永业在从地方回府城汇报工作途中被捕,敌人害怕雷永业进行革命宣传,便给他灌了哑药;接着,对冯爱媛施以酷刑,妄图从她口中得到我党组织名单和活动情况。但冯爱媛宁死不屈,直至被押往刑场,还在向路边群众宣传党的主义,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共产党胜利万岁”等口号,最终慷慨就义。
再如当时琼崖妇女解放协会的主要领导人陈玉婵。她因遭叛徒指认而被捕,入狱后,敌人几次向她打听组织情况,还引诱她说:“只要你不搞群众运动、声明退出共产党,又愿意当司令的太太,就可以出去住楼房、坐小车,好日子长着呢!”没想到陈玉婵坚决不肯就范,拒绝透露党的秘密,并怒不可遏地回答:“你们不要看错了人,荣华享乐我不要,我要的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要我当司令太太,除非日头西出!”恼羞成怒的敌人对她严刑拷打,数日后将她残忍杀害。
还有原琼崖妇女党员代表、中共广东省委委员林一人。她曾在1929年春被国民党军警逮捕,面对威逼利诱坚贞不屈、滴水不漏,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被营救出狱后,她在琼东一带的农村继续化名潜伏,开展妇女运动,后为掩护其他同志撤离而与敌人英勇搏斗,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在危难时扛起担当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侵华日军的战火愈发密集,短短两年便烧到了海南。其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海南党组织反复进行清剿,当地革命力量严重削弱,党中央书记处便指示要以全岛为对象发展党、发展武装、发展民运。已有革命底子的琼崖妇女很快行动起来,有的负责宣传,有的参军入伍,积极参与各项抗日工作,书写了一段段动人往事。
这一时期,从女青年、女学生到女战士,都秘密而积极地参与到创办抗日刊物和其他宣传工作之中。其中,当地地下党领导的“前哨社”创办《前哨旬刊》,专门围绕抗日救亡刊发尖锐泼辣、鼓动性强的各种文章,办刊、撰文者便以妇女为主流。为了支持抗战,不少妇女将自己的儿子、丈夫、兄弟送上战场,干部群众为此还创作了许多感人至深的“送郎歌”,以“自古尽忠难尽孝,上阵冲锋莫退身”这样朴素而有力的唱词鼓舞了无数战士。
妇女参军也蔚然成风。1939年琼崖抗日独立队正式扩编为独立总队,总队、大队、中队及医院、机械厂的炊事员全由女性担任,各大队的医务人员也都是女同志。为了隐蔽,部队时常通宵行军,到达目的地后,普通战士都安排休息了,这些负责后勤保障的女同志还要负责找粮、放哨、照顾伤员,十分辛苦。时间一长,不少女同志都出现了肚子肿大、脚肿烂等问题,但她们从不叫苦,仍竭力为部队奔波。
一些女同志从事情报交通工作,更是艰险无比。那时,日军在琼崖各县实施封锁,部队的男同志往往很难进去,即使进去了也很难开展工作,女同志们便采用各种形式潜入敌占区完成任务。比如被琼崖人民亲切称为“姨母”的刘秋菊,一次,她收到敌人准备扫荡我根据地的紧急情报,为确保组织能有足够的时间转移,便决定化装成奔丧的寡妇,沿途敌人见状大叫倒霉,并不盘查,如此一来她很快就把情报送到了组织手中。交通员张玉英也多次机智地完成了组织任务,日军抓不到她,便将她的丈夫等家人全部杀害,她化悲愤为力量继续坚持工作,在一次送情报归途中不幸被日军发现,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除此之外,在统战工作方面,女同志利用亲和力强的优势,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方式瓦解敌人,工作虽然辛苦,却也取得了突出成效。比如文昌县四区区委的女同志们就混入民工队伍进入了日军炮楼,结识了日军某据点的翻译官手岛,后经仔细工作,争取其充当我方内线情报员,从而全面掌握了该地日军动向。
可以说,女性的聪慧、灵活与执着、坚韧,在琼崖抗日斗争史中体现到了极致。为守护党的秘密,无数革命女性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比如原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随军服务团团长许如梅,被捕后敌人将她的衣服剥光、放狼狗乱咬,逼她供出县委机关地址,可她始终只有一句话——“不知道”,临刑前她更是慷慨激昂地说道:“砍头只当风吹帽,革命自有后来人!”乐万县交通员卢爱梅在工作途中被敌人逮捕,敌人对她施以酷刑,甚至用火烧她的身体,但她始终不肯向敌人吐露组织秘密,最后被活活打死。
坚定地守护党的秘密的,还有许多普通海南妇女。为更好地掩护抗日战士特别是保护伤员,不少妇女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将自己的家建成了供战士们活动、暂居的“堡垒户”。据统计,抗日战争结束时仅在海口市琼山区就有“堡垒户”247个。有的妇女在家里挖了地洞,白天让同志们躲在洞里,晚上出来活动。为了让伤员睡好,她们不仅把床让出来,还把家里的门板拆掉给大家垫着,自己和孩子们却睡在地上。文昌县的云四婆、简锦婆、郭冠英等是著名的“堡垒户”“革命母亲”,她们都曾遭到过敌人的威逼毒打,但始终守口如瓶,没有说出过党的一丝秘密。
坚定地走向光明
革命斗争的道路虽然遍布荆棘,却指向光明。党领导的妇女运动打开了海南妇女的新世界,她们切身感受到跟着党、拥护党,再苦再累也是一个大写的“人”,因此始终坚定地与组织站在一起。抗日战争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悍然发动的内战,当地广大妇女不畏艰险,又迅速投身于新的斗争之中。
在党开展的各项地下工作中,妇女继续发挥着突出作用。特别是澄迈县地下党员孙玉梅和临高县船主黄金女勇敢机智地先后几次出海,绕过敌人海上封锁线,把党的领导干部送到海北,使准备渡海的十五兵团及时掌握了海南敌兵分布和我方情况,以及其他重要情报,为我军胜利渡海解放海南立下了不朽功勋。依据这些情报和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的意见,我海南作战指挥部最终确定了“分批偷渡与最后主力强渡相结合”的正确战役指导方针,并决定在风向等航行条件转变前发起大规模渡海登岛作战。
与此同时,对岸的海南妇女也已经做好了秘密迎接解放军的准备。据曾在琼崖特委妇女筹备委员会工作过的何佩玲老人回忆,发动妇女的工作是一层层布置下去的,特委工作人员到相关县进行总体部署和动员,再由县里一层层地下达工作安排和计划,由此来控制知悉范围。妇女们的重点任务是参加担架队、医疗队,以备不时之需。此外临高角是解放军预备登陆的重点地区,当地党组织除了组织妇女做好部队后勤外,还安排了一些妇女在这一带走村串户,寻找迷路的战士并妥善安顿。一次,一支部队刚上岸,就被国民党军发觉了,接应的妇女立刻把解放军藏到附近的丛林里,国民党军搜了半天不见人影只得作罢。
据当地党史记录,虽然当时解放军与海南妇女语言并不相通,但大家见面时都感到分外亲切。在各方力量的团结下,我军顺利登岛,并强力突破国民党军防线,随即纵深挺进,横扫全岛。5月1日,海南岛全境解放,海南妇女也彻底迎来了新生活!